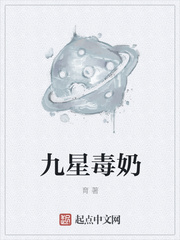看书阁>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的人是谁 > 第26章 大宋第一军事强人(第1页)
第26章 大宋第一军事强人(第1页)
午时已过,考生们陆续交卷离场。
有的面带喜色,有的愁眉苦脸,还有的聚在一起讨论刚刚的策论,争得面红耳赤。
陈书文是最后一个交卷的。
他将答卷整齐叠好,毕恭毕敬的递给收卷的吏员,转身往外走时,却被吕余庆突然叫住:“小友留步。”
陈书文停下脚步,诧异行礼:“学生陈书文,见过考官大人。”
“敢问小友师从何人,竟这般年岁便来参加科举,实属难得。”吕余庆捻着胡须,目光温和。
他以为陈书文是某个当代大儒的弟子,故而好奇一问。
“回大人,小生目前在养正书斋,先生乃是郭知远。”陈书文如实答道。
养正书斋?郭知远?
吕余庆捻着胡须的手微微一顿。
养正书斋的郭知远他知道,不过是一落魄举子而已,启蒙尚且有余,但要说能教出陈书文这等弟子他是万万不信的。
“在如此年纪便有这般见识,难得,难得。”吕余庆不住的点头,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许:“且待放榜吧,老夫盼着你的好消息。”
若是这娃过了府试,到了省试依旧是他主持的话,这娃便可以算作他的门生了。
“谢大人谬赞。”
陈书文面色平静再次行礼,转身离开了贡院。
待陈书文走后,吕余庆开始逐一阅卷。
有些卷子只扫一眼,便知一塌糊涂。
字写的如蚯蚓漫爬,文不通,理不顺,看了只觉得污眼。
能入目者,寥寥无几。
“一群不学无术的樗栎庸材!”
越往下看,吕余庆越是气不打一处来,甚至忍不住骂出声。
其实倒也不怪这届考生素质太差,在五代时期战乱频繁,科举也并非按期举行,甚至有时候正考着试呢,出了考场才发现,改朝换代了……
再加上那时多数底层百姓入不敷出,活着都难,能上私学的多数都有家底在,这类人也不会走科举之路。
所以从军之人远大于科举之人,且良莠不齐。
但道理归道理,吕余庆还是想不明白,怎地有人连题目都看不懂,就敢来考功名!
让你议农桑利弊,你给我写经商之道?
让你论吏治得失,你给我拍什么马屁?
更有甚者,洋洋洒洒写了千字,全特么是生僻字,你在秀什么?
吕余庆越看越是来气,真想把那作卷之人喊来狠狠打几板子。
这时候,他似突然想到了什么。
在一堆卷子下翻了翻,最后拿出陈书文的那卷。
字迹工整,文通理顺。
先前粗看一次便觉得极其不错,如今细细品味,更是觉得惊艳之极。
吕余庆不禁挑眉。
“有点意思。”
再看一遍。
“很有意思!”
片刻后,他叠好陈书文的试卷,贴身收好,冲小吏说道:“备马,吾要入宫一趟。”
…………
皇宫,紫宸殿内,檀香袅袅。
赵匡胤正与赵普商议着要事,眉头紧锁,时不时敲击着案几。
“陛下,吕事中求见。”内侍轻声禀报。
“吕余庆?”赵匡胤愣了一下,随即道:“让他进来。”
片刻后,吕余庆快步走入殿中,躬身行礼:“臣吕余庆,参见陛下。”
“何须多礼。”赵匡胤摆摆手,“朕记得你不是在主持开封府试,怎地这个时候来见朕?”
吕余庆起身,脸上带着难掩的喜色:“陛下,臣在府试中发现一篇极佳的策论,特来呈给陛下一观。”
说着,他伸手从怀中拿出陈书文的试卷,双手奉上。
内侍接过,转呈给赵匡胤。
赵匡胤接过试卷,漫不经心的展开,目光刚扫过开头一行,便微微一怔,坐直了身子,神情渐渐变得专注起来。
一旁的赵普见状,也好奇地凑了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