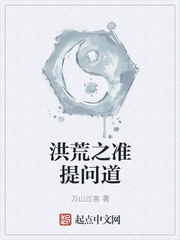看书阁>状元郎 > 第五十章 第一课(第1页)
第五十章 第一课(第1页)
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,反正苏录听下来,觉得朱山长的话还是蛮有道理的。
科场上也不存在突然开窍一说,都是日积月累,硬桥硬马的功夫。所以要是被证明真不是那块料,还是早点放过自己,找个班儿上吧。
就像山长最后所言,若想不被淘汰,就力争上游,把每一次考试都当成生死关口吧!
山长训完话,负责三个斋日常教学的斋师,还有各位教专项的先生,也都跟学生见了面。
然后三位斋师便将学生带回各自斋堂。
省身斋的斋师,正是苏录考帖经时,那位神情严肃的监考老师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襕衫,须发也有些花白,名叫张砚秋。
张先生简单的自我介绍完,就每人发了一张尺二长的白竹纸,让学生们默写学规。
苏录赶紧打开文具盒,取出砚台和白云笔摆好。来不及磨墨,又从书箱底部抽屉中,直接拿出墨盒,蘸着现成的墨汁写起来。
前几天他就发现,明明过年忙得十多天没空写字,重新拿起笔来之后,字反而进步了一截,有一种突然开窍的感觉。
之前他总是纠结于某一笔的长短,或某一字的偏旁位置,却忽略了整体的气韵、结构的平衡。比如楷书的‘横平竖直’并非绝对平直,而是靠细微的倾斜形成视觉平衡,这一点在埋头苦练时,他就一直把握不好。
谁知抽离了一段时间再回归时,他居然跳出了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’的窠臼,一下就明白如何从整体出发调整书写了,终于有了一点书法的意思。
将学规默写完之后,苏录吹干白竹纸上的墨迹,满意地端详着自己的作品。
忽然他发现,张先生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,忙起身轻声道:“先生。”
张先生按住他的肩膀,示意他不要起身,低声道:“默写的都对,只是这笔字,还得好好练。”
“是。”苏录不禁老脸一红,哪还好意思跟先生说,这还是自己最满意的一回呢。
张先生又背着手,在讲堂中来回走动,看学生们的默写情况。
确定都没什么问题,他便命他们将此学规,贴在各自的床头,每日自省,千万不要违规。
“书院里规矩大过天,一旦违反,轻则鞭笞,重则开革,谁也救不了你们。”他语重心长地嘱咐自己的学生。
“是,我等谨记先生教诲。”学生们忙齐声应道。
接下来,张先生又讲明了本年的课业安排。
“今年一年,你们都将学习四书和八股。如无意外,每日上午讲书四节,下午教授作文。课后会留作业,同样要认真对待。”张砚秋叹了口气道:
“山长也说了,学规上也写了,两个月后的三月十五,将进行句集注》,显然大哥那套也是一样的来路。
“这套书是书院发给你们的,接下来三年只有这一套。损毁遗失的话,只能自己花钱再去藏书阁买了。”张先生嘱咐一句,便不再废话:
“打开《大学章句》,上午还有点时间,可以给你们讲两段。”
苏录赶忙从书盒中拿出那本崭新的《大学章句》,掀开句集注的缘故。
先生之所以还要逐句讲解经义,一来是担心各处蒙学塾师水平参差不齐,教得五花八门,所以得统一一下版本,以书院教授的为准。
二来,侧重点有所不同。蒙学要求学生‘字字能解、句句能通’,注重的是基础。
书院则站位更高,张先生通过分析经书的‘圣人之言’,让学生掌握孔子训诫的口吻,和孟子辩论的语气。这样学生才能在作文时,学会把自己当成孔孟,避免以自身视角阐发议论。
因为八股文自‘起讲’部分开始,就须‘入口气’了……即以孔孟程朱等先贤的口吻说话,便是所谓‘代圣人立言’。
就拿这《大学》的第一句为例,便听张先生缓缓讲解道:“此句阐明我儒家‘三纲领’,非但提纲全文,更挈领《四书》。”
“因此,这里‘入口气’的核心,就是抓住‘纲领、教化、庄重’三点,以‘圣贤立言’的高度,揭明‘大学之道’的本质,显儒家圣贤教诲,而非个人见解。使人明晓‘为何学’、‘学什么’——如此,方能贴合《大学》的圣贤口吻,做到‘口气即义理,义理即口气’。”
只上了上午短短一节课,苏录就明白了,为什么大哥说,不读太平书院就考不中秀才了……
此中的门门道道实在太多太深,没有明师指点,你一辈子也想不明白,更学不会。